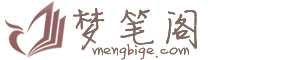日里金华盛开 星夜钟声都无
作品:《花人间老酒楼》 茫茫大山亦时无常,
棋海飞棋来落有序
此间界年朝法无考。
王曰:“士权商财,二择其一,卿当以为”
有道是:“缘聚了大桌满人”
“何小旦说书喽”
说书人不过二十来岁,正是年轻盛颜,却穿的一件蓝白衫,还是一件白蓝衫,真色早已不见。手上一把古黑的铁扇,看来是锈迹斑斑,灵用不灵用,始终在说书人手中,是个宝贝。
八个月前,一张海告:“岁寒有三友,贤名松竹梅以我荼芙之名,今我睦和学与微州城州学同邀天下群士相聚直伏山以文会友,与松竹梅为要共一场三友文会。文会举三贤,赠君子三宝原玉一枚,薄绿杯一对,玲珑巧冠一只,又另摆红宴,联绝对与众笑谈”海告一出,几乎轰动,一夜之间,满城爱好风雅的或文人c书生莫不是知情,不出半月,消息便传遍了南北。更有坊间多传:“此乃四城第一才女招亲之告,荼芙是谁荼芙是四城第一才女,公认的第一,听说其幼童时期,被笑问一时狂傲情真竟说出:嫁与天下第一人这样话来小小稚言,可见其品性高洁”“近几年来,朝廷每年科举,选拔的人才中有大半来自睦和学,是以睦和名声日渐高升,外界自然也跟着敬重起来。”
在这之前,四城第一才女名声在外早已是外界对睦和各式向往倾慕。如今,这海告一出,原来以文会友本是文者读书人间酷爱的一件雅玩之事,它如以武会友一样,舌战中不打不相识。此番,更不知有多少同道中人期待着与睦和的这场三友文会。非仅此,睦和同微州城州学办的这场三友文会,它出现空前带了一场盛会。这盛会受万众瞩目不少的豪富紫贵之家,或是小小名望之辈,大商贾,官员,山下平常人家,都赶来旁看,远道而来的更是带着一家夫人孩子,使得直伏山人集顶了,而睦和这个大学园也一一从容接下。
睦和学坐微州城直伏山上,近年来声名鹊起,为邻城八方州学推为第一。直伏山山体独秀,奇名闻世。
睦和学,先见是:“睦得万卷书理达通天倒海终一出门,和到言行四方记是非黑白莫变颠倒。”再见,一半人高石墩坐着日晷,也有小字,“山水养人,草木育人,成在半山,学与盛世。”这外而内,大为前后两处,前处又学堂,学舍,书楼三大处;供夫子,学子学习作息。后是后府,茶园。凡宾客来睦和皆住后府,有睦和师长亲自接待。后府是师长的安家之所,一般学子们是不轻易来的。
说睦和的学子舍处,此时到三友文会已迫在眉睫,但学里总有几个人总爱在这么关键时刻惹出各样是非睦和学里也是一样不能幸免。
“哟,乔飞,你这钱袋可真别致,真好看,你不是说你们家没人了吗这谁做的啊”与钱袋并榻头是两套叠齐的学服,两幅字画。听这欠收拾的口气,必是罗元。
罗元是睦和三夫子的独子,睦和一共六十三位夫子,唯这三夫子最好性子,是以深受爱戴。也许,父待子苛,罗元对自己的这位父亲满心敬畏。在三夫子面前,罗元便是正派小书生,一离了,本性皆露。罗元嚷着乔飞放在心头之物,说也就罢了,竟还动上了手,直接抢了乔飞钱袋,举在高高上。那是一个极精绣钱袋,清新淡雅,用的兰花色线,绣的喜得连科,可见做这个钱袋人的用心,正相配了得这个的少年郎
乔飞原伏小案专心抄默,罗元这么要闹,哪里允许放肆当即,就要把钱袋夺回。罗元不给,两人围着屋里追闹一圈。“罗元,你别动,你放下。”
屋里五张榻,每张榻前都有一张小案,上面多少放有学子的纸墨,书文,更有两个学子,一个正练着书法,一个正做着注解,也被动参与到这二人大战中间。虽是一小会,那书法都变了样,那注解更是狂花了一笔,惹得人怒,一个大叫:“罗元,”一个破骂:“罗疯子,闹好了没有”这还有一张桌,在进门口那儿,特别安静,也十分安立,也有一个学子坐在那,坐的端,手捧书文,脸上十足的认真和仔细,一点儿不受打搅。对于罗元的各种意外,这人向来是受之不惊。
追闹一番罗元才罢了手,停在一高处,大喝一声:“好了,给你。”乔飞接住又坐回小案来待继续抄默,忽并道:“这是我邻家的姐姐做给我的,你们可不许乱拿。”如下命令一样,下给了罗元同屋里人。
罗元方从榻上下来坐乔飞榻上,依不饶道:“呵,邻家的姐姐漂不漂亮”
乔飞一脸防范:“你嘴里又想使什么坏,她有亲的。”看乔飞一脸紧张,罗元心满意足。
在夫子眼中乔飞不算出尖也算也可,在学子中间乔飞于爱玩者不厌,于爱学者不嫌,倒不是乔飞自来圆滑,是乔飞真诚也勤勉。这样人儿,时不时叫罗元爱逗上一出
成平日里取乐最有趣的一个。
“有亲了什么人家”写书法的停下笔来问道。
“萧周问的。”罗元生出满脸无辜,直指萧周。却不知为何,此时却怕惹恼了乔飞。仿佛在萧周问时,罗元好像看到乔飞自己都未察觉的一闪而逝的阴云。“萧周好不知趣”罗元暗里骂道。为何这样,罗元不知。罗元虽爱玩笑取乐但心地纯良,罗元的玩笑从未叫人真到难堪
乔飞似打抱不平:“什么人家不知,我又没见过,听是门当户对的,不过提来就气,说好的,是姐姐十五岁时就来迎娶,这都过了一年了,他们家早下了聘,姐姐这里又不能接别人的亲,他们家人又没了踪影,哼,等将来,我考中状元,必要替姐姐出这口气”
萧周诚恳,人小胆小好贪玩,最是义气:“那好,要是我中状元,我也来帮你出这口气。”
罗元替屋里人算齐,也道:“哎状元只有一个,我中了状元,到时候你们进士都跟着我,由我带你们一起去出这口气。”
乔飞哪可置信:“你你规矩都没学齐,要是尚言还差不多。”说话一眼看去那边独坐一桌之人。
尚言答了一句:“这可不一定,或许予阳他有个好哥哥,又是真正的书香子弟。”几字话尚言说来,相与几人慢了许些,但听来却如律乐一般极舒服。
罗元欠收拾的口吻又来,过去着:“是啊,这个注解,就是你哥专门让做的吧还是从我爹那儿直接借来的,予阳,你就跟宠宝似的,这么大人还处处被看着。”罗元这回欠收拾说的非常有味儿,硬是生生活把予阳说成好似一个小女儿家似的,处处被看着犹有娇护之意。
这无疑叫予阳有些恼,当即断止:“说什么呢你”不料满屋子都笑。
外面,天很好。草木叶青,晴和无风。
尚言从不轻易大笑,只笑在脸上无声,任何时都这样。萧周笑来倒声没多大,捂着肚子,很快的便笑去了,笑净了。罗元大肆笑,声清未达洪亮,不到癫狂。乔飞向来温笑,偶有笑出轻声,却仍衡君子之态。予阳此刻仍是恼红了脸,少年的面子总是要薄,少年的心也总是很嫩,少年的羞态也是最满。若可以此时予阳也跟着笑两声,然后学着罗元的话叫罗元找洞去,叫众人再多笑一阵,叫不见轻易大笑的尚言放肆一回,叫乔飞笑来不顾一切,便是丢掉君子之态又何妨人在时,就该狂笑。哪至以后,想到这一回,竟止不住的泪如雨下
予阳并非一个规矩少年,相反他从没有安分过,他一惯来做过的出格事太多。
但也同样,罗元是三夫子的降中物,降予阳的,便是他哥。
予阳对他哥也是又敬又服,这让他每次被说到他哥时,都自发的本能堵塞。从而使他面上形态既惹人好笑,又惹人忍不住暗里直喊怜乎众人都知予阳姓李,李家世代生长江宁城,早些年家中有人做了大官,后来落没留下藏书几万,是以尚言说道,李予阳是真正的书香子弟。李予阳父亲李仁善才德兼备也是当今世上少有的能士之一,平时修身养性从不张宣,为人也谦。现在为江宁城县官,这官来得也有些渊源。外公风田牙是大商,已故。母亲风秋美明达事理,通晓词律,终福寿浅。风田牙生年想膝下二女无丁,故要大女婿入赘家门,只在侍奉不在延姓。
正当屋子里笑意浓甚,门外闯进来一人,脸色惨白,身躯微颤,似在极力抑制,屋里少年并未注意起这不样征兆。大伙儿,尤其罗元更是上来打趣:“方礼,你是真弱体质,这么点路去了那么久回来还带这么大喘气儿脸都煞白。你呀,确该多去常大夫那儿,多补调养还能讨教些药理,又能多见常蕙姐姐。”
“怎么样了”是乔飞急切的关问随后到来。
方礼一进门,屋里人皆围了过来。
尚言也起来道:“别听他胡说,你去看金桥,他怎么样了”
方礼张开嘴,顿了一会,才恍若神来:“噢,没事。”再不说更多了。
屋里人都松了口气,罗元道:“没事最好,我就说嘛跟我们一块蹴鞠,怎么可能被予阳的一个鞠球打中心怀就倒的是他自己本身生病的吧”
乔飞跟着想道:“他本身心中就有些郁闷,蹴鞠玩开心时身累,都怪我没事带他打什么蹴鞠”说话中捶了一下桌子,桌子闷哼,乔飞恨恨直咬牙。兴许是被乔飞那一锤震到了,方礼本望着那桌子忽而完全找回了心神,再道:“他是有些暑罢。”
萧周吃惊:“中暑中秋已过,怎么会中暑呢”
方礼并未理会,而是看起李予阳来:“予阳,那日我同你同说起外公,你好像是说你外公是个大商还很有名望,你还说你希望同他一样,你是不愿科考入朝的,我当时笑你,不过现在一想,行商和做官没什么区别,只要喜欢就行,你何不就此出去行商去,依你外公昔日名望和你家中底厚,我想应该不难”
“你乱说什么”罗元几乎吼道,屋里也一下静悄。
尚言亦言:“这
不行的。予阳要是行商,李晓学兄不也不能再入仕途,我朝不似先朝,明法规定:官商无亲,若兄弟二人一人从商,另一人也不得入朝堂,一宗家中,一人从商,皆不得入朝堂,除非罢商三年,方始重入。况,予阳的父亲现正是江宁城知县。他去从商,岂不连累伯父弄不好唉方礼,你方才话大大不妥。”说到这里,一向想事更为深层,竭尽周全的尚言再无言语可言,直退一边,背向众人,同罗元一样被方礼方才的话所震动,莫名气着。
几人一年入学,十分交好,虽时玩笑,也相问关切。方礼方才那话实在有些逆众,叫听人一时不,是恨不能接受。萧周便不知言语了,乔飞极应:“是啊”李予阳奇怪,平时一向中居的方礼,怎么说两句连尚言听了都冒出恼来的话。尚言一惯清楚理智的。
李予阳笑问:“呵,怎么了好好的怎么说我出去难不成金桥说,暑消去要打我不成”
乔飞站出来:“不会的,金桥不是这样的”
乔飞自小没了父母,家中留下钱财受旁人打理,虽不愁吃喝,但是亲情难盼,看来是个哥儿,可也是约束的很。金桥也年纪小小跟着大伯在越门,为越门公子陪读,母亲与妹妹在乡下也是亲离两地,虽是书童,却是十分聪颖,与别个书童不同。两人从一初识起,便惺相怜惜,十分要好。因为乔飞,金桥也与这屋里人相近。
方礼急言:“金桥当然不会可他是越九英的书童”几字几乎都是从心底吼出来的,方礼还从未吃过如此虚慌,尽管如此仍强力压制着,一屋少年也并未有人看出端倪。
罗元又上来:“你是怕越九英报复,给金桥出气来找予阳麻烦我可不当越九英是什么越门中人,什么界内的小舅爷,什么大家口里的天之骄子,这又如何他再显赫也终究是我睦和的学子,还能在学里生事不成。”一通话说的无暇,接的恰好。罗元只当方礼惧怕越九英,屋里人这么听下来也都认为了。
萧周也道:“他不是和李晓学兄一样也要参加三友文会哪里还有空管得上金桥我想三友文会过了,他大概才会知道金桥的事,那时,也不存在追究了,想他九岁能被特许进入睦和,不只是天才,也自有一些宽度对称才是。”两句话说完,一时没人再言。萧周心地最是善良,又相信人有作为必有其德。
还是李予阳道:“原是担心这个金桥也没什么事说来我们家和他们家还有段渊源,他们家还欠了我们家一处大情,若为这事越九英跑来与我叫难,实太不明智,他多聪颖一个人岂会这样做”这原来是宽慰话。
罗元听的好奇,忍不住问:“唉他们家欠你们家什么情我小时候听家里老人提过,说越九英的爹越山前辈,和你外公风田牙前辈,一个是微州城甲商,一个是江宁城甲商,两人亲似兄弟,后来不知为何,渐无来往,越山前辈也在我朝初定时举家搬到临都城。”
“这个”予阳实没想说,正这时,云宽巾带月白服,纱薄大衫,清晰可见内肩侧绣金字“睦和”,有青叶纹痕绕行,华彩不溢满是蘅香。发上束系罗紫缎带,此是睦和三年学子所用。再看屋里,方礼之外,李予阳几人,穿着各样,头上一致青麻缎带,此是睦和一年学子束带。睦和二年学子的束带是枫红,四年学子的束带是缎雪。睦和学服是不轻易穿出的,只在盛大日子或是贵宾来时,才会整齐穿戴,一般是睦和的理事学子常常穿着
这位来的理事学子,进门便熟络打趣:“怎么都站一处是又出什么祸开集体大会了”话来十分自然,想这屋里人在学里的活跃非常。
屋里人一同见礼:“子末学兄。”
子末姓魏,名申字子末,面似清泉,言笑春风,在睦和素有蛮威之称的二夫子门下。
罗元接道:“子末学兄,我们能出什么祸这三友文会上上下下都有我们的差事,忙都忙不过来哪里出祸要是办事不力的祸,那得另当别论。”
魏子末故道:“是吗”再言:“我刚刚知道你们踢了一场蹴鞠,忙都忙不过来哪里踢的蹴鞠”学着罗元的口吻。
罗元失惊:“子末学兄,你都知道了”
魏子末道:“我是知道,也不是人人知道。太宁学兄大概不知,也就没人来罚你们了。”魏子末想是给这屋里一众少年下了一颗定心丸却不知这屋里刚才都红了脸,此时任什么太宁学兄谁还顾上
太宁姓楚,在一惯谨肃的大夫子门下,性子疾厉有点合二夫子,大多一年二年的学子,同极少的三年学子,都被楚太宁青着脸训教过,也都在怀疑太宁学兄是不是拜错了夫子就是楚太宁的同辈和前辈都有这样认为,楚太宁对同辈有过冷脸规劝,对前辈出过冷言建议。楚太宁的一腔正义言辞,叫人听也不是,不听也亏。楚太宁自身学识渊博,这渊博最具有说服力,楚太宁也并非一个恃才高傲的人。此番,三友文会楚太宁出人意料并未参加,说是已志在教学。
尚言道:“子末学兄来可是有事”
睦和大多事务都是交由学子打理,夫子照看。从二年始
锻炼学子的处事变能,到三年学子可以独立承事,进四年学子要迎备科考,和初入学一年学子一样,重心学习,不同是一年学子偶有被叫去协助二年或三年学子,而四年学子则只一心专考,不再问事。睦和是二年,三年学子主事。
魏子末道:“事有一件,红前宴空缺人手,罗元,尚言你们二人在三友文会过后立刻赶去帮忙准备红前宴。还有明日四更忙过南围大场,李予阳,萧周,乔飞,你们三个帮忙去布置完南围岚,然后,才去吃饭。”
尚言答应:“是。”
萧周犯嘀咕:“南围岚不是师姐的丫头带香和师娘身边的环姑姑布置吗南围大场已有三百人众,若是需要我们三人完全可以调去,也可以早点吃饭啊不必一定要忙过南围大场再去南围岚。”
魏子末道:“夫子安排,我们做大家辛苦了”说的随意。
萧周忽听,紧张不得了,才想到刚才自己自言自语的,一个“是。”抢急忙慌道了出来。
魏子末没揪着说什么,却望了李予阳,同样自言自语起:“荼芙师姐也着男装参加三友文会,外面虽不知,不过我倒是好奇,师姐和李晓谁更胜一筹诶,李予阳,你倒是说说,荼芙师姐跟李晓谁最后夺魁”话中直逼李予阳,一番戏谑。魏子末同罗元倒是有些脾性相同,只是这二人一个是静水,一个是涛浪。终究是,魏子末年长几岁,而魏子末也只对李予阳这般,这不知为何倒是每年睦和内都有一场大比,魏子末在李晓那儿回回都是满身灰。
李予阳这次没给脸的道,淡漠的口吻直言:“子末学兄不也参加三友文会,自己怎么忘了睦和人才辈出,难道风头都是我们的外面没有更胜者吗”
魏子末很是意外,迟迟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学的好。”才一番夸了,再又自己作小声:“谁惹了他了”瞥见罗元嘴角上扬。
恰时,传来钟响,响了五声。萧周道:“饭时了”
尚言亦问:“子末学兄,同我们一起”
“不,我还要去五夫子处。”魏子末说着。
“事化没”罗元脱口而出。
魏子末正当离去,忽听罗元言语,驻足问道:“你说什么”罗元不语,魏子末继而道:“别当我不知道”
罗元忽而抢道:“话梅的味道,你闻”
魏子末了然于胸,无奈看着:“夫子是夫子,他教授我们,我们应当尊重,这为人之道上必须的。”说完,魏子末便去了,也不理会这屋里人有几人听到。
尚言戳穿:“这种时候,哪来的话梅”
罗元满不在乎:“子末学兄都没有揭穿,你又何必说”尚言也就不再多言。
方礼看着李予阳,一直发愣。眼里红丝,神情疲惫,想什么不能,魏子末的到来已经把一切都推后了。
自饭时钟声敲起,睦和各处汇出一股人流。天上的云霞翻涌,黄昏近晚。照在睦和清泉溪池里,叮叮咚咚只闻得声,依伴的老柳渐照不得自己的垂影。天上连最后一点颜色也不得见睦和便恍如一条盘卧的大龙,只剩下似鳞的烛火随处跳跃。这烛火晃晃忽明忽暗,在静悄渐闻不得虫鸣鸟叫,只有花语淡淡芬芳时,一盏一盏挨个着去了。也有一整片儿的,一小圈儿的,无声悄去,不疾不慢,数来竟是数不清恰好似哪个天神作的词曲一般。这天神想必也有些糊涂,或是定然困急了,竟也零落了几个叫这几个鲜奇过了头,直等着天明,使人掐送回来。另外的,三两个一处仍勤勤巡巡像逛园子一般满学游荡。这是睦和值夜的守卫。然而,这夜,没有天明。
一个穿着护卫装的青年男子,支倦桌上,守在滴漏前。一声嘀嗒下来,这护卫正打盹憨香,梦中寻一个好睡的姿态,不禁移了手,头悬磕了一个空,猛的痛醒,这才看到漏上时刻。“四更四更了”随即,忙忙拿上铜锣到一年学子舍间徘徊走动,当然,不能惊动别的地方,如后府。
“四更四更四更天了”
有些屋子立刻就亮了灯,有些懒懒不动,也有些迟延干脆就在黑里摸而当锣声每在一个舍院敲起,邻房两屋总有学子相互敲门。
李予阳,罗元这里,门不知被谁先开了,大开着。屋里只点了一盏烛,靠门边四方桌上那一盏不明不暗。
五张带背床榻,榻背上罗元刚拿起衣裳,急急忙忙:“快快快,不能迟,待会可是要被问名的。”尚言依是稳若,在镜前理装束发。李予阳正打结系带,刚套上大衫。萧周洗过脸便走过来,一边往自己身上挂一个黑木圆牌,上面写有:睦和一年,萧周。这圆牌是行走在睦和学里每个学子随身必带的。此番三友文会,睦和虽是广邀天下群士,但睦和学里却是有严格的甄选,除非天才如越九英,不然大多还是三年和四年的学子参加,二年极少,一年更是没有。
萧周看着李予阳,笑嘻嘻来:“予阳,咱们学服你穿着,宛如天人,走出去叫人一看,都分不清到底是衣衬人还是人衬衣果然,人生得俊美就是
不一样”
这番经过盘旋的夸美在李予阳听来只是一问:“你想干什么”
萧周笑:“我想去茅房。”
李予阳道:“正好我也要去。”
两番话落入罗元的耳里,罗元那里正绑上青麻缎带,忙笑来:“萧周,你那么好玩怎么如此胆小小心我和你讲过的,茅房鬼。喔”并使坏鬼叫两声。
叫的萧周直喊:“罗元,”
李予阳也道:“罗元,你别吓他,这也怪不得萧周,他家教太严。”
萧周顿时皮道:“哼我才不怕呢我有予阳,而且天就要亮了走吧”
“嗯。”李予阳轻应了一声。
听罗元在里面问来:“哎乔飞呢”
尚言对答:“他是你啊早早收拾好走了。”
出门,一抬头,萧周叹:“啊星星,没想到,竟是满天星星。”是啊李予阳跟着也抬头望了一眼,今夜不知怎了竟是满宿齐全。
睦和学里,晴天的夜里,路上总会放一两盏灯,睦和有能人测得星云,知得风雨。睦和花树众多,走来一路,也叫人神清气爽,甚是好闻。
茅房这边相较空落,有一颗老树,十间连上一排,李予阳萧周来时还见有两个学子疾行出去。
萧周早起总要上茅房,每次都要拉上李予阳。时间长了,李予阳便也有了这个习惯。过了一会,李予阳从茅房出来,望了一眼附近,一个人也没有,抬头看了天上,星星倒是还在,远处稀稀点点的灯光,李予阳好像看到人来人往。
李予阳熟悉的坐倒老树上,这次感觉似乎等了有些久,便叫了声里面:“萧周,好了没”里面对答:“没有,起不来了”李予阳问:“什么起不来了”萧周道:“好像拉肚子,一阵一阵的,哎哟,痛啊。”李予阳神色凝肃起来:“怎么这样,刚才不是好好的吗”萧周道:“我也不知道啊”随后又道:“你还有没有草纸”李予阳:“哦,还有两张。”随后掏出来从缝里递了进去。想了又想道:“这样不行,我去找常大夫给你拿些药丸来。”里面喊住:“哎,”李予阳当萧周是怕了:“你别怕,罗元的话你只当没听过,我很快回来。”萧周再道:“不是,后府大门有亩伯看着,你要是去了,定惊动夫子,我们现在肯定已经迟了,南围大场三百人众,待我稍好一点,混进去,定不会叫发现,你这一去,可就,”萧周痛的冷汗直冒,在里面已经大气喘着说不上话了。此时此刻,还想着迟到,自觉理亏,也只有实诚的萧周了。
李予阳稍一想:“你放心,我不走后府大门,也不被巡卫发现,我知道,从竹里苑能更快更近的到常大夫家,那里有一道矮篱笆,我只跨一下就能过去,那里原是先荼老师长一位僧友居住,现在人去房空,我很快回来,也定叫常大夫决不跟学里提起,咱们一起混过去。”听到萧周又道:“好,你小心。”李予阳才去。
萧周也不知为何,突然心里慌张的紧,这慌张甚至有那么一瞬掩过了腹痛。
竹里苑,门上寥寥草草,是那几个字。苑门失修已久,瘫在两边,一道矮篱笆半人高在星夜下,大约可见轮廓。左边房屋,右边一大片竹林,深不见底,那后面是悬崖万丈。整个苑里,新老嫩幼各样竹子都有,这里唯不见其他树木。
而直伏山上也只有这里才可瞧见这些竹子天生自来,白日照见生的滴翠华莹。睦和的第一人荼老师长正是看到了这些竹子,才爱上直伏山,与友人一起并决定把一生的志向投在直伏山成了睦和学
李予阳几乎是跑着来的。数步之外,眼见着竹里苑,稍息慢走过来。忽然,一声声短促:“来人啊来人啊”
李予阳心头一动,一步跨进门里,一大片竹叶的清香而来。
闻着熟悉,李予阳看见,矮篱笆上,一个人影跨了过来,却因种种几乎是全身摔了进来,一时吃痛,不能爬起,只喊道:“救命救命”
李予阳听出来了,乔飞的声音。同时,他看见,矮篱笆上方,满天的星色逐渐退去照见一个诡面人,似流云一般飞了进来。
李予阳感觉不对,不论是乔飞的救命还是睦和的规定,未得允许,外人禁入。他都要必要告警,“咚”竹里苑大钟敲响了。李予阳要敲满三下,视线里,一把利刃九转飞来,只是一瞬间。虽看不清利刃的模样,但李予阳知道是个伤人的东西,显然,诡面人也是不愿让他继续敲了。他想先避开,还是划破了脖颈,虽只是擦伤了皮,但还是一阵火辣。又恰好碰到了一排竹竿,他无意拿起一根粗壮的,冲去诡面人跟前,一个撑跳,挥举起横挡两人中间,李予阳恐吓:“你是什么人你要再不走,刚才的钟声你都听见了,只要一会,就会有很多人来。”语气是何等冰凉,竟连李予阳暗里都吃了一惊,诡面人并没有说话。
忽听身后人站起来叫:“予阳,”
“乔飞是乔飞吗你怎么会在这儿”李予阳问道,目光还是警惕在诡面人身上,毫不松懈
乔飞缓缓道:“我来看金桥。白日里,想着方礼的话,越九英不好惹的,虽然萧周说他天才自有些度量,但是我还是想找金桥告诉他叫他不要让越九英找你的麻烦,可以,也不要叫越九英知道”
李予阳再问:“那后来呢你见到金桥了吗这个人怎么回事”说实在的,李予阳当时就说过金桥也没什么事还为了让几人宽心,说了越家欠自己家一个情。可这些少年是怎么回事一个一个的,操上心。越九英怎么越九英多可怕多不能惹李予阳真想问问,可这时,他最先要知道的是现在。
不等乔飞言,诡面人似笑道:“见到,哈哈你已经把金桥杀了,他怎么可能见到”
李予阳吼道:“你胡说,你根本都不认识我怎么知道我的事”
诡面人道:“我是不是胡说,就看你记不记得你蹴鞠的时候,做过什么你是怎么打中金桥的心,叫他瞬间气绝的。”
李予阳听着,握竹的手不禁收得更紧,手心几乎出满了汗,他的背上也奇怪的凉飕飕,似沾惹了万颗水虫,他不是相信诡面人,他是在怕诡面人说的一个事实,他想到白日里方礼的模样,他
乔飞大喊:“予阳,你别听他说,金桥真正是”
哪知李予阳一听,立刻就问道:“真正是什么”刹那间,李予阳看见乔飞神色大变。糟了,心里喊了一句。手上竹竿瞬间一断为二,一截落地,一截从他手里入了乔飞的胸膛,他这才认清楚,这竹子是被削了尖的。同时,他也看到所谓的诡面人原来不过是带着面具的怪物怪人。若这削了尖的竹子,是插入自己腹中,那没命的便是他了。
怪物却没那么做,却在他耳边近乎一种邪魅的声音来道:“第一次尝到血的味道吧”“要好好记得。”竹叶满地,一阵劲风踏来。
刹那间李予阳的惊慌失措,只有怀疑的望着,化木似的愣着。
乔飞仍强着说道:“我没事,不是你,真的,不是你。”明显的,满眼都是害怕,明显的,知道自己不行了。
李予阳不知觉的湿了眼,嘴角一动刚要说什么,那阵劲风来到他后颈边上,似想阻拦,却误将李予阳打晕过去。
不知来人是谁李予阳能听见两个人的交手,感觉自己倒在一股热液里,是腥甜黏稠,“好像要天亮了。”乔飞微弱的声音。
竹里苑是个一直干净的地方。
乔飞颤抖的手,血红的手,从自己怀里掏出一件东西,原是那个精绣钱袋,都因血色而丢了本来面貌。“予阳,”乔飞喊道。予阳没有回应,乔飞只好把那样东西放进予阳的里衣里,然后拉予阳的手,叫他紧紧拽住,这一刻,乔飞才知道,自己多么想念,姐姐。乔飞喊着:“帮我帮我姐姐。”乔飞自己听在心里,好似多大声,而清冷的早晨却并没有听见。随后,那只血红的手从李予阳手上滑了下去,落在自己的衣摆上,和圆牌并在。怵目惊心还有两个字,在李予阳的手里“不责”划满了笔数。而眼睛,盯向东方,一丝红色隐隐现来,一滴眼泪拼尽了力从眼角露出留给这世间。
不知多久,李予阳恍惚好像看见有人走过,然后口里一阵苦麻,接着一阵后:“哎,学子学子,”他勉力睁眼,一阵白光,什么也没看见,彻底昏睡过去。
竹里苑仍是一个一直干净的地方。
三友文会如期而来,直伏山上彤云笼罩。
方礼躺在房里几日,虽不见外面,但从听的也知道一些风光。一阵一阵咳嗽上来,方礼只觉晕眩。方礼病了,“看来还是要去常大夫那儿拿点药。”方礼说着。随着起来,穿好了衣裳,缓缓走了出去。此时天才刚明,外面一个人也没有,大家都还酣睡香甜,方礼悄悄带上门。心里想道:先到夫子那里告会一声。
路上,方礼见到一个人急冲冲的从另一条路跑了出来,方礼本想叫住,奈何这人跑得太快,而自己又病得虚晃,也就作罢。一时又想:常大夫家的辛哥儿早早来做什么这条路只能去夫子那里,难道夫子病了想到这里,方礼便顾不上自己,勉撑着要急急赶过去。睦和学,学子拜在哪个夫子门下,便叫这门夫子为夫子,虽其他门夫子也来相应传授,却是叫二夫子三夫子。
方礼挨上夫子的院墙停了下来,大喘了几口气,才又慢慢走过去,额上身上大汗淋淋。
方礼才走了两步,便听见辛哥儿哭腔:“几日流食还可咽下,汤药也可吃得,只在刚刚,喂他些水喝,喝不得了,把我吓怕,一时奔了来,付甲之先生,通知他家里人吧再延迟,只连最后一面都没了。”
什么方礼大吃一惊,暗想:这次又是谁
清晨的微明,照见几个人身上一重青色。
付甲之沉华丰实,两袖浑圆。方礼看过去,大夫子今年约有五十了吧还是那段名师风骨,叫人肃然起敬。
付甲之道:“再半日,再多半日”说不清的,此时付甲之眼里的神色。是暗淡是悲伤是光是希望无法琢磨。
辛哥
儿忍不住的扭头揩去眼眶里的热泪,恰好瞥见方礼,便喊了出来:“方公子”付甲之也转身过来,直视方礼。
方礼极度虚弱,仍是先行了礼才道:“告假几日,仍觉虚乏,这一早是来请示夫子允我去常大夫处拿几副药回来。”
付甲之望了许久才点头道:“如此,你同辛哥儿一道。”
付甲之说完,方礼犹豫道了一个,“是。”便让辛哥儿扶着,两人背去。心里却惶惶不安,方礼直觉耳边有一道惊雷。一个声音,不住的说:夫子方才一直看着我是叫我去通知那病人的家人吗夫子是知道我刚才听到的话所以把这个事落给了我怎么会我分明一字未提假作毫不知情。是方礼也觉自己想多了,而在久经世事人面前,方礼还是差了。也不知不觉中接下了这个差事,在知道病的人,方礼不得不接下。
既然已经在假装,方礼在路上便就不会再问。
山中翠景,十分好眼。两边山草灌木,显见一房屋舍。抬头是天地阔然,低头,脚踝没在野花草丛之间。那方不远地,可见断崖。
常大夫家的门是虚掩着的,辛哥儿推门,方礼进来,院里石桌安好,只太过静悄。三间连房只中间一个开着门,房里大药橱挡不住放出光。厨房药香也出来,里面没有人影,倒是火炉上时不时迸出两声。
方礼问道:“常大夫,常蕙姑娘都不在吗”
辛哥儿答道:“师父师姐和你们的荼姜大管事都下山寻药去了。”
“是吗”方礼忽笑问。
辛哥儿一脸诚挚:“什么是你们师娘常年疾患,此番更来汹汹。”
方礼无力道:“算了,是不是无关了。”
辛哥儿又道:“我看你倦得很,先睡会吧”
说话间,辛哥儿已带方礼来到大药橱边上一张小榻前。为方礼看过脉,顺手拿了一瓶药丸,倒出一粒,与方礼吃了。见方礼熟睡去,才起身来。是另一张榻上,也一个人。
方礼直睡过了午时才醒来,醒来辛哥儿又立刻拿了碗药给喝了,这一睡,方礼精神好了不少,辛哥儿看着也放下心来。
“什么时辰了”方礼问道。
“午时刚过。”辛哥儿回道。
辛哥儿弯身把药碗放下,方礼一眼看见睡在对榻上的人,几乎几步并作一步跨去。
“予阳李予阳他怎么了”方礼不能相信,方礼自小体弱多病,自通了一些岐黄,不等辛哥儿来说,自己急急查看。而后悲痛上来:“怎么会这样怎”“是他,是他,他知道,他知道。”方礼摇头,看见付甲之,一个劲的要摆掉。不忍相信
辛哥儿直在一旁:“方,方公子”吓得不轻。
方礼却像听不见一样,吼道自己:“不会的,不会”随即跑了出去。身后不顾辛哥儿的叫唤:“哎方公子”心里直问:为什么想到大夫子说,再等半日,想到辛哥儿哭腔,几日流食到连水不能再饮,方礼心中一阵火烧。
这一回,方礼不走后府大门。从竹里苑直奔去了南围大场,不只在快,方礼似乎在刻意,这样好似把自己的愤怒到痛恨给表现出来,然而最终,方礼只能做一件事。
三友文会,几日光景,却当真是叫人觉得几世难得四里一派和象,人人谈落到,如何如何未见人的独解,流芒的文词,让人端来细赏回味无穷。此间雅怀,茶交相互碰撞。更是宾客们足乐一惯世嚣缠怨,都让尽山外侯着
南围大场,方礼所见,已成散场一片,到处都是学子文衣,名流一派,睦和学服来往从中忙杂。
方礼来时,不经意间与罗元,尚言擦身而过。罗元,尚言正疾步而去。两人还一路说着。
是罗元道:“这次三友文会真是大开眼界,想必予阳现在一定是心里乐开极了,他呀就是高兴也在嘴上憋着样子可好笑了哎呀都怪这么多人我这几日竟是连他的一点身影都没看见等我见到他,一定好好戏他一番。”
“是啊”尚言缓缓道,眼中多是慕光。
罗元又道,忽然把尚言抓住,停了下来:“不行不行,我等不及要戏他一番,咱们不如找他去”
尚言拉道:“此刻要去帮忙准备红前宴,再有两个时辰,红前宴就要开了,不如等红前宴上你再找他一戏”
罗元不甘道:“红前宴上,咱们睦和的学子不是人人都去得,再说,红前宴上不能尽情放肆,在那里戏他不痛快,又少了萧周乔飞,他们三人好好怎么晚上都去守书楼了”
两人一边往前,尚言又道:“五夫子临时安排,书楼人手不够,毕竟那里住了许多来参加三友文会的友士,你挨到晚上我们去那儿找他们出来也是可以。”
罗元听后又高兴起来:“唉我怎么没想起把他们叫出来然后咱们到屋顶上去,跟以往一样,也不祸害别人,又能痛快一番,极好”
“嗯。”尚言应了一声。
两人行之一段,闻
来阵阵清香甘醇入鼻,都不觉浓吸一口,尚言说道:“到荼芙师姐的茶园了。”一眼斜睨那方,是几亩茶地,一颗老榕,一个丫头探出,四方张望。屋门檐前落有几棵香树,时不时盛树之芳参渗其中。这便入了后府。
罗元神秘:“荼芙师姐和李晓学兄,真真是一对金玉。”
方礼还在南围大场,四处徘徊。忽然,方礼抓住一个从身边跑过去的学子叫道:“庆亮,你有没有见到李晓”
庆亮见到方礼,一脸欣喜:“方礼你病好了”随着伸手摸了方礼的额头,被方礼拿下,听庆亮又言:“你也知道咱们的李晓学兄夺了魁元的事也是,这是咱们学大事。荼芙师姐还夺了第三元呐唉莫怪是要嫁就嫁天下第一人这也非天下第一人不能娶啊那第二元是两个并列的,一个长相玉郎,一个戴着东西说是脸上不好,不知长相,声音极好听。”庆亮开口就如江河,滔滔不绝,直把三友文会风头全说尽了。
方礼喃喃道:“我们的李晓学兄夺了魁元”
“嗯,”庆亮点头,随着又道:“我赶着去红前宴帮忙,不和你多说了。”说完,便又跑开去。一会儿,不见了。方礼仍是:“原来李晓是夺了魁元”这也就想明白了过了片刻,方礼才惊起:“这会这么多人,到哪里去找李晓我虽见过两面,却也是匆匆忙忙。”方礼瞧着,这一处,那一圈,方礼见到夫子宾客一堆,看到穿着素华的师长,正被一老爷模样的人叫道:“伯老师长,此番三友文会真是极好”
伯老师长也不过五十多岁,却满脸沧桑,回应道:“如今是才子辈出实不相瞒,此番三友文会却是了了我平生夙愿,我从少年就希望有一日似这样齐聚一方。”
方礼离开这里,再看南围大场。
方礼好像失了听觉,只凭见的,四面都在谈笑风生,到处是质气独各的才子文生和一片睦和学服。
方礼迷了眼,突然,喊了起来:“李晓,李晓,李晓,”边喊边往前走,同时,也让众人都看了过来。
李晓还没喊出来,一个极冷肃的声音先出来了:“大呼小叫的做什么”这声音做了些压制,方礼还是一听便知道了。方礼认得,也熟悉。
出声的人在人群中间,头上系的是睦和的缎雪。方礼站住了,随后,方礼又听见来自背后另一个声音先叫道:“太宁学兄。”
瞬间,楚太宁对这人一个眼神的交汇,便不再对方礼再说什么。
浩浩人群,方礼回头,独见一个睦和学子,束的罗紫发带,腰上悬三连玉珏,右一块深玉,瞧一身的气宇乾坤紧在那眉额之间,尽显尽了灵秀。方礼愣神一刹,好似恍过世间一切,真正见了一个天地男儿。
待到人问:“找李晓是有何事”方礼才醒悟。
李晓两边各有一人,一个瘦单英秀,另一个,布衫清扬。
方礼走上两步,近了些道:“予阳出事了”
“在哪里”李晓问道。
方礼仍一脸正色,不容置疑:“常大夫家。”
随即,李晓转身对身边布衫清扬人道:“京生兄,稍后我再带你一览睦和。”又往楚太宁那里告知:“太宁学兄,我去一下来。”京生自是豪言应道:“好。”楚太宁也微颔首答应。别的众人则是相继奇道:“怎么了”“是出什么事了”这些都不是已背去的李晓和跟去的方礼及瘦单英秀之人要看顾的。
那瘦单英秀之人见李晓忽去,呼怪同去,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原来方礼同李晓的话,恰只叫李晓一人听见,方礼却不是有意瞒了众人。
李晓离开南围大场,一阵风来,南围岚里一条黄巾飞出,与之擦臂而过。
另一处,一个人也被叫住。晴阳下,这人的影子短了一半,凭着声音是魏子末叫道:“九英。”
影子转了个身,同道:“魏申兄。”听这声,像还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少郎。
依是魏子末声:“有你家书。”
影子递出去,影子接到。影子拆看,影子手在抖。而后,家书落地,同着一句:“舅舅,”,影子只剩一个。魏子末瞧着,那家书上只两个字:速回。
李晓站在李予阳榻前,李予阳身上着的不是睦和学服,不知是谁的李晓认不出来知道不是李予阳的,李晓又见到李予阳的脖颈上有一道划伤,已结痂了,李晓伸手去探摸了一下,李予阳身上热烫上来。
辛哥儿在一旁道:“病了几日,高烧不退,我是没有办法,师父不在师姐也不在,又不让请山下大夫,人这么烧着,恐怕了”
“你说什么”李晓脸色几乎都是变了。
瘦单英秀之人一惯尖刻,直道:“你少危言耸听谁不让请大夫”而后又对李晓道:“兄长,你别听他胡说,他一个小药徒,待我去请一个山下大夫来。”
辛哥儿仍是道来:“自你们的三友文会开始,他便一直烧睡着,不曾醒来,你们还是早早打算带他回去。”
李晓不信,这好好一个少年似辛哥儿那话谁也不信,李晓轻声喊道:“予阳,予阳,醒醒,告诉我,你怎么样了”李予阳丝毫不答应,李晓放在自己身上的手不禁攥紧。
李晓道:“你说他病了几日,怎么不早点来告诉我就放他这样他若有个三长两短,我定不罢休”忽转疾言:“子争,收拾一点东西,我们即刻下山。”
争却迟疑:“可,可是,马上就红前宴了此刻下山”
李晓只顾得,拿一旁的凉水一个劲的为李予阳去热,又道:“去找胡莱借马车,顺便叫他告诉夫子,禀明这里一切。”
争又道:“红前宴不去可就”
“快去。”屋里一震,方礼和辛哥儿顿时都像不必呼吸似的,静悄静悄。争还是等了一下,争还从未见过李晓有任何的大喊,何况这还是吼叫。
争仍还是道:“我不是不去,是我也可以照顾二阳,我可以带他去找大夫,红前宴你”
李晓打断道,声平如往:“我不会安心的。穆争,家国天下,国之为先,家之为二,孰轻孰重,不要我说。予阳生死未知,我怎能不在”
这家国天下,国之为先,家之为二,还有一句,穆争知道,穆争明白,穆争去了。只道了一句:“子争知道了。”
穆争去后,方礼过来:“李晓学兄,你方才说不罢休,可有想过你这几日风光予阳凶多吉少,夫子是知道的。”说到这里,却不必再说。
李晓带着穆争,李予阳下山,穆争驾车,一路直来到微州城一所医馆,穆争把车一停,急急忙忙拽了个经验的大夫出来,李晓让大夫看李予阳,大夫却看一眼:“这不行了,不中用了。”
“大夫,你给他看看,你还没看呢”李晓抓着大夫不放。
这大夫道:“我已经给他看了,你们送来太晚了,我看不了。”
李晓仍是不放道:“您都看不了,还有谁您是大夫”
这大夫又道:“老夫是大夫,老夫惭愧诶这天下有个人你们可以去找他他是大夫之首,人称寿有医师。他住在青山,常年在外,四海行医,不晓得现在在不在家。他要是不在,你们可以在青山上找一个肖前辈,听说这个肖前辈曾经是他的一个外门弟子,家里也是世代行医,医术神化,只不过这个人有个怪癖,只要你们不是江宁城人”
穆争问道:“江宁城人怎么了我们就是江宁城人。”
“我也不知道,”这大夫道:“江宁城人要问祖父姓名。”随着又道:“也没关系,只要与官无亲也好办。”
穆争冷色,穆争心里大夫应是最仁心的,何以仁心,手握生死却各样端摆
“我们是江宁城人,我们家老爷就是江宁城县官。”穆争道,言语间毫不客气。
这大夫一时也不知怎么说了,忽然就觉肩上一阵疼,直嚷道:“哎,这位公子,这位公子哎哟。”直到李晓收过神来放了手,这大夫才叫唤一声。李晓道:“多谢告知。”又对穆争道:“这位肖前辈,我略有耳闻。子争,给大夫诊费,我们去青山。”穆争见李晓神色一反往常,很是担忧,什么也说不出,就掏钱。
“哎,不必不必。”这大夫推着。
穆争道:“你就拿着吧,我们也耽误了你一时半刻。”
这大夫接过,随着从袖里掏出一物,取了一小粒,放在李予阳的嘴里含着,道:“这个叫凉快丸,我自己做的,你放他嘴里含着,每一个时辰一粒,只当死马活医,虽是没什么用,却好过什么都没有,你们这一去青山也得一天一夜,只希望,他福大命大,能熬得去。”说完这些,大夫目送他们而去。
马车刚走,一对夫妇带着自己的儿子,哭着过来,妇人泪眼汪汪:“何大夫,你快帮我们看看,我们家这孩子被学里送回来,学里说他是夜里起夜,被猫吓着了,学里说回来休养,可你看他像个痴呆。”这人却不是别人,正是萧周。
何大夫安慰:“别着急,别着急,进来我看看你们二位对孩子是出了名的严厉,这孩子从小就被你们吓破胆了。”门前一下落了个清净,何大夫这间医馆,叫何济堂。
梦笔阁免费小说阅读_www.mengbig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