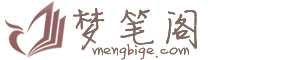88.汤圆
作品:《医食无忧[穿越]》 ,最快更新医食无忧[穿越]最新章节!
如果你看到这行字, 说明v购买比例小于60%, 此为防盗章
对二娘这副药来说,前后二次,各煎一炷香的时辰也就差不多了。
余锦年在灶旁点了根香作计时用, 便又取出另一只砂锅来,想煮一壶醒酒汤。
这醒酒汤古往今来有许多种类,有饮酒前预先服用以防醉酒的,也有治疗宿醉翌日头痛干呕的,种类不一。他今日要煮的汤名为“酒夫人”,是戏说这汤如家中夫人般温婉贴心, 知冷知热, 其实是很寻常的一种醒酒茶,饮来不拘时候,其中用料也不过葛花与枳椇子。
枳椇子这味药因现代不常用,好些药店都不卖了, 在这里倒是寻常可见,因其长相扭曲怪状,民间也有俗称癞汉指头、鸡爪果的, 好听些的则叫金钩梨,是味解酒良药。而另一味葛花更是有“千杯不醉葛藤花”的说法。
余锦年抓了三钱枳椇子,杵烂了, 与两钱葛花一起煎煮, 小厨房里很快就升起了浓浓的药香。
窗外明月高照, 这时一道黑影静悄悄穿过隔帘, 在院子当中停下,仿佛是采纳日月精华般定定地站了会,又转头朝着亮着昏黄橘灯的厨房飘去。
余锦年饮了不少酒,厨间又暖和,在灶边拿着小蒲扇打了一会风就犯了食困,忍不住昏昏欲睡了,他这边刚顿了个瞌睡头,灶间门口便飘来个黑咕隆咚的影子,将他直接惊醒了。
夜幕星垂,秋虫低语。
那人逆着月光倚靠在门框,面如冠玉,形容却意外地凌乱,且口中微喘,好像是被什么追赶着来的,本来高束在头顶的发髻不知何时被他折腾散了,头冠也不知掉在了何方,一头乌发垂瀑在肩上,隐隐遮着一侧脸庞。
余锦年愣愣看了看他,刚唤了个:“季公子?”
对方没听到似的走了进来,坐在余锦年斜后方的一张小杌子上看余锦年煎药,正是下午穗穗搬出来撕侧耳时坐的那张,小木杌子本就是穗穗专属坐骑,对他这样身材颀长的男人来说着实小了些,致使他团在那里很是局促,也不清楚是不是因此而不开心,嘴角微微沉着,也不说话。
这人又是怎么回事,难不成是一个人在前堂还怕黑,非要追着光亮追着活人气儿走麽?
余锦年手里攥着蒲扇,被盯得如芒在背,简直奇怪得要冒冷汗了。
煮着醒酒茶的砂锅中咕噜噜又滚一开,余锦年忙掀了盖搅动一番,见差不多了,用抹布裹着烫手的砂锅耳朵,滤出一碗汤汁来。
季鸿在后头看了,嘴角沉得更厉害了,简直要到了苦大仇深的地步。
葛花和枳椇子俱味甘,因此这汤药茶虽呈茶褐色,实则并不如何苦涩,余锦年看他深恶痛疾的表情,也不愿与醉酒的人计较,自觉又从橱柜中抱出一罐蜂蜜,淋了两勺后拌开。又自院中舀了些井水,隔碗浸着降温,因为酒性热,而醉酒之苦又多是湿热作祟,因此醒酒茶汤之类皆是稍微放平冷了一些才好入口。
季鸿垂丧着头任他来来去去,想把自己藏在阴影里别叫他看见才好,直到那茶碗都端到自己鼻子底下了,忽视不得了,这才抬起了眼睛,盯着端碗的那只手看。
“季公子……季鸿?”余锦年举得手都累了。
季鸿听见自己名字,僵掉的眼珠子才动了两动,他使劲抿着唇作痛苦万分状,好像余锦年端的是碗烂泥臭虾汤般,他挣扎了会,才似下了好大一个决心,皱着眉头问道:“非喝不可?”
余锦年点点头:“非喝不可。”
两人互相瞪视着,谁也不让谁。可惜余锦年是个脸皮厚的,任季鸿拿万年寒冰似的眼光在自己脸上刮,也仍是笑吟吟地举着碗。他们就此僵持了一会,余锦年拗不过他,只好做出了退步,与他商量道:“这样如何,我喝一口,你喝一口,若是苦了,你就吐出来。”
季鸿想了想,觉得这很公平,不吃亏,于是眨眨眼表示同意。
余锦年抬手将茶碗在嘴边飞速一比,就往季鸿脸前送去,道:“该你了。”
季鸿皱眉:“你没喝。”
余锦年企图哄过去:“我喝了。”
季鸿很执着:“没有。”说着身子朝前一倾,贴着少年的嘴|巴嗅了嗅,眉心一蹙,眼睛里带着一种“看吧被我抓住了你就是在骗人”的无声谴责,更加确信地说:“就是没喝。”
“……”余锦年被脸前酥|痒的气流扰得一怔,还闻到了季鸿身上一种淡淡的熏料味道,可偏生此时季鸿满脸的无辜状,似受了骗而委屈兮兮的孩童一般,让人不知如何应对。他生怕季鸿又凑上来闻自己嘴巴,忙往后撤了撤,实打实地喝了一大口,才将碗推给对方,见季鸿扔一脸怀疑,哭笑不得道:“这回真的喝了,你总不能再到我嘴里检查吧!”
季鸿看了看他唇上沾着的亮晶晶的液体,很是不满地接过碗,拧着眉头盯着碗里药汤看了许久,才探出一点舌尖沿着碗沿舔了舔,在嘴里品一品,尝着确实有甜蜂蜜的味道,才不甘不愿地喝下去。
余锦年见他如此地怕苦药,心中忽而有了主意,想出了明早要做什么小食来。
季鸿呆呆地捧着碗,看他从柜中拖出一只袋来,里头是红红的豆子。
这豆子就是常吃的红饭豆,而他前世以讹传讹说有剧毒的其实是另一种植物,半红半黑名为相思子,才是“此物最相思”里的正主,食后肠穿肚烂,但别看它有剧毒,在部分少数民族中竟还是一味难得的险药。这一想又忍不住想远了,余锦年忙用木盆盛出几斤红豆来,洗了两回去掉杂质,再加井水没过豆子,准备泡上一|夜,明早好做炸糖饺。
炸糖饺本来并不费功夫,就是那普通饺子皮儿包上白糖馅,过油炸至金黄即可。不过余锦年要做的炸糖饺里头,可不是包白糖那么简单,他打算做个红糖陈皮豆沙馅,既有甜爽口味,又能有理气健胃的功效,面皮也计划着揉两三个鸡蛋进去,擀得薄一些,这样糖饺儿被热油一炸,会愈加的酥口薄脆。
他刚筹划好,灶台上的第二根计时香也燃到了尽头,炉上药罐里咕咕噜噜喘着白气,将盖儿顶得叮叮响——二娘的药也煎好了。他抽了灶下的火,用抹布包着手将药汤滤出一碗,与二娘送去。
临走前,余锦年特意看了眼小杌子上的男人,见他困倦地沉着头,还是有些不放心地说:“灶上还烫着,季公子你可千万不要乱动,等我一会儿回来便送你回去。”
谁知这一去竟耽搁了不少时间,原是二娘觉得口渴,又因为夜重了不愿再叨劳辛苦了一天的余锦年,便起身喝了两口桌上的冷茶,这一喝不要紧,反而牵扯出了老毛病,胃痛万分,余锦年敲门进去时正好看到二娘靠在床边疼得直冒冷汗。
余锦年忙从柜中拿出一条手巾给二娘擦汗,扶她上|床歪躺着,给按摩了好一会的止疼穴位,又聊了会子天转移二娘的注意力,等她好容易觉得舒服些了,好歹能露出个笑容来,才嘱她将药喝下,看她慢慢侧躺下迷迷糊糊地睡了,才悄声退出来。
也不知二娘还能有几日了。余锦年长叹了口气,一时也有些伤感。
这一折腾就是半宿,等余锦年在困倦中想起自己似乎还忘了个人,忙不迭地跑到厨房里看那人还在不在的时候,发现季鸿竟然依旧端坐在小杌子上,腿上歪斜着一只空碗,头也垂靠在旁边的柜边上,沉沉地睡过去了……也不知这男人怎么就这么老实,叫坐哪坐哪,叫等着就等着,动也不动。
哎,且当是,一壶浊酒喜相逢罢。
余锦年弯下腰,用自己纤瘦的小身板架起季鸿来,踉踉跄跄地送到了自己的房间,给人脱了靴子外衫,松了松里衣系带,还体贴地给人盖上被子,又怕盖多了闷着酒气不好发散,这一番伺候下来,自己简直跟是人家小媳妇似的了。
“你也真是心大,就这样睡在别人家里,早晚要被人卖了。”余锦年摸着他褪下来的衣物,都是软细滑手的上等料子,哼,若是遇上个心贪不正的,这时候就该把你扒光,衣物细软拿去典了,人卖到莳花馆里去。
莳花馆是信安县最红火的一座南馆,男色对大夏朝内的达官贵族来说只是一种雅痞,因这几年“有的人”在青鸾台上风头尽出,却只留下一段飘渺无踪的传说,反而更是点燃了那群纨绔贵族们的好奇欲,像季鸿这样贴合传说的“仙风道骨”款的漂亮人儿正是眼下最受士族贵子们欢迎的类型。
这些都是有次莳花馆里的跑腿小童来买糕点时多嘴说来的,余锦年闲着无事便多听了两句。
他自然是不可能真的卖季鸿的。
“哎呀,所以说,心地善良说得可不就是我么……”余锦年喃喃自恋两声,打开橱门掏出另一套被褥来,往床前地上一铺,就算是今儿晚上的床了。
刚舒适地闭上眼睛,抓住了点周公的衣角,就听见头顶传来几句呢喃,他以为是季鸿醒了要喝水,也知道醉酒的人缺不得水,不然这一整夜都会渴得焦躁,便摸黑起来,盛了一杯温水,将季鸿扶在自己肩头,一点点喂他。
但别说,这人虽是又醉又困,浑身软绵绵的架不起来,人却很是乖,余锦年叫张嘴就张嘴了,照顾起来不怎么废功夫。窗柩间透进薄薄的月光来,洒在季鸿裸|露在外的脖颈与锁骨上,泛出玉白而又微粉的色泽,正是说明他身上酒气在渐渐发散。
余锦年搁下茶杯,刚要钻回自己的小被窝里去睡觉,季鸿突然就将他手一把抓住,紧张喊道:“二哥!”
走在出城的路上,季鸿看着少年挎着篮子,大摇大摆洋洋得意的样子,不禁暗中质问起自己,方才是怎么中了他的招,被一道剁椒鱼头给骗出城了的?
余锦年走着,抬头看了看太阳,他上一世听养父讲过老家里造房的一些琐事,听说会热闹得像过节一样,便十分想见识见识,不知道这里是不是也一样热闹?眼下看日头约莫已到正午,便不禁加快了脚步。
今日出城的人好像格外多,各色车马人流都拥挤在西城门口,余锦年身材瘦长,三两下便窜了过去。季鸿看他像只灵活的小松鼠一般往前跑,只见一抹藤灰色的袖影自手边掠过,他下意识去抓,却扑了个空,一眨眼少年就没影了,只余周围一张张喧闹的陌生面孔。
这一瞬间,季鸿感觉到心底泛起一种淡淡的失落感。
他随着人流慢慢地挪动,刚出了城门口,远远就听见略带惊喜的一声:“季鸿!”
余锦年朝他使劲招手,将他从人堆里拽了出来,又似乎是怕再被挤分散,便径直拽着他往前走。季鸿跟着余锦年的脚步,越走越快,最后竟一路小跑起来,两旁枝叶稀疏的柳树在视野中迅速地后退,一转头,就能看见大片大片的农田。
好像很久没有这样跑过了,众人只道他身体弱,不能四处走动,于是长久以来,他都是静坐在书案前,一坐便是一整天,敞开窗看的是精致得一成不变的园景,关上门便只有案前永远开不出花儿来的垂盆兰。
尽管他喘得厉害,肺中因突然的跑动而疼痛,季鸿却觉得心中甚是舒畅,好像身体上覆着的那层厚厚的尘埃全都一扫而空。
如此跑到吴婶娘新宅前,这新宅位置很好,不远处就有附近沥河的分支流过,远远就见院子里头已经来了许多人,正热热闹闹地起哄。一个方脸的匠人正高坐在梁上,裸着一条肌肉攒生的结实臂膀,面前捧着一只大簸箩,扯着嗓子朝底下喊:“要富还是要贵啊?”
下头屋主人乐呵呵道:“都要!都要!”
旁边的吴婶娘也高兴得喜笑颜开,她这一回头,瞧见余锦年二人,忙招呼他俩进来:“正抛梁呢,快来快来!”
两人穿过层层叠叠的人,望见正中梁木垂下的一条红绸,很是喜庆。他们两走进去后,便先去与屋主人道喜,却没注意到原本闹哄哄的人们在他们背后窃窃私语起来,有人悄悄拉了吴婶娘,朝着两人中的其中一人努努嘴,问:“来的这是什么大人物?”
吴婶娘想了想,以前在一碗面馆好像也没见过这人,于是笑笑说:“……大概是帮厨罢。”
众人打眼望去,那男子身姿挺朗,姿容隽秀,虽面若含霜显得高冷了些,却真真是玉质金相,再看旁边那个个头稍矮的,则更亲和些,也是俊朗郎一个少年。若是连两个帮厨都是这般风度,那他们这家子请来的大厨得是个什么样了不得的人物啊!莫不是城里春风得意楼的大掌厨!
大家私底下本就在传,吴婶娘家男人能发财是因为请到了真财神爷镇宅,再看今日如此做派,更是对此事深信不疑,纷纷鼓起斗志,打算抛梁时要抢得更多喜果以沾沾财气。
此时梁上的匠人晃了晃怀里的簸箩,簸箩里头是些糖果子、喜花生、糍粑、馒头之类的,便是即将倾抛的喜果了,都是象征吉祥如意的东西,那匠人抓起一把往下抛来,笑容满面地喊着吉祥话:“来咯!先抛一个金银满箱!”
见旁边不管男女老幼都忙不迭去抢,余锦年也伸出手来,可没等果子掉他手里,就被别人给拦截了。
只听头上又喊:“再抛一个白米满仓!”
随着一声哄笑吵闹声过后,余锦年看着自己空空如也的手心,咬了咬牙,就差一点就抢到了!
那上头的匠人也看到下面的余锦年了,他个子瘦小,被其他村夫农妇们挤得东摇西晃的,遂遥遥笑道:“小哥儿,别心急,还有呢!看着啊……这回抛一个财源滚滚八方进宝!”
余锦年本来对争抢喜果的事没什么太大兴趣的,但是连抢了两回都没抢到东西,这就像是娃娃机里投了币,而娃娃却被挡板卡住了出不来,是一样的感觉。他自己憋闷着,却不知惹得乡亲们如此疯狂争抢喜果的罪魁祸首,正是自己身旁亭亭而立的季大公子。
季鸿低头看了身旁少年一眼,见他好像跟什么赌气似的微微捏着手指,这几日他见惯了少年的笑脸,此刻看到少年生气的模样竟也觉得挺有趣的。
这回余锦年还没伸手,身旁就有道身影往前站了半步,扬起了袖子。只见季鸿轻轻踮了下脚,就从半空中捞到了什么,他还没展开手掌,余锦年立刻眉开眼笑地扑上来,直问他抢到了什么。
季鸿被扑得向后一踉跄,甚是无奈地把手里东西伸出来——是一对染了红点的喜花生。
吴婶娘探头看了看:“花生好啊,长命富贵!”
突然,不知从哪里蹦出来两个七八岁的皮小子,正是七岁八岁狗也嫌的年纪,大笑大闹着一把从男人手里抢走了刚得来的战利品,抢就抢罢,还回过头来朝他俩扮鬼脸,好不嚣张!余锦年当即手快地捉住了跑得慢的那个,拎着小子的后衣领,脸上笑容都没散去,问道:“还跑不跑了,还抢不抢别人东西了,嗯?”
熊孩子两脚扑腾着,抬起眼想求助,却正对上季鸿淡淡的似乎要把人冻成冰柱的视线,顿时嗷嗷求饶:“不敢了不敢了!还给你嘛!”说着便挣脱开,将东西往余锦年手里塞去,撒腿就逃跑。
只可惜其中一颗已经被不小心捏碎了。
余锦年剥开另一颗,抬手往季鸿嘴里一塞:“给你,长命富贵呢!”说着嘴里嘟囔道,“本来咱俩一人一个的。”他也并不是真的信吃了这颗花生就真的能长命百岁,只是有点不高兴被熊孩子抢了东西这件事而已。
季鸿错愕地含着一颗花生,跟着余锦年后头走进了厨间所在的西屋。
灶里头已经燃上了火,旁边木盆里摆着清理好的整鸡与猪肉,余锦年蹲下来将鸡与肉提起来查看了一番,确认都是新宰杀的鲜物。刚才在院中他观察了一下,角落里有大概三四张叠起来的木桌,想应是晚上待匠用的,这每张桌上总得菜品齐整,有荤有素才行。
余锦年心中正盘算着要做些什么菜色,就见季鸿若有所思地走了出去,他也没管,兀自拿刀来将鸡去除内脏,打算与他们做个一鸡三吃。
这些鸡都是自家散养的土鸡,肥嫩却不肥腻,肉质看来还不错。而所谓三吃,便是一只鸡做出三种吃法,至于是哪三种却没有固定的路数,则要看做菜的人的心情了。因为外头的都是些做惯了粗活的匠人,对食物的要求不比县城中人细致,更多是追求腹中的饱涨感,余锦年的想法是一半白斩一半红烧,而剩下鸡头鸡爪及大骨架则继续炖汤。
他先烧上水,水里投入几大段葱姜以去除鸡腥味,少量黄酒八角以提鲜,煮鸡最关键的是控制火候,使水热而不沸,这是为了使鸡肉鲜嫩有弹性,他这边刚将整鸡没入水中,季鸿便回来了,问他去做什么了也不说,一副高深莫测的模样。
余锦年没问出来,便郁闷地指使他去洗菜,而自己则打了盆沁凉的井水,继续做鸡。
白斩鸡在南方菜系中属于浸鸡类,须得将鸡在热而未沸的水中浸煮片刻,再提出鸡来在冷水中冷却,最后再入热水中焖煮。以前余锦年总是嫌弃煮白斩鸡麻烦,但此刻他是为了生计而辛劳,反而觉得心里充实,更是愿意将自己最好的手艺呈现出来。
他把火停了,鸡则留在锅中焖上,便出去取季鸿洗好的菜。
这一看不要紧,季鸿两脚湿透地站在菜盆边上,一脸严肃地盯着手里的芹菜,然后面无表情地“咔嚓”一声,拦腰掰断了,之后随手将芹菜带叶儿的那半段扔在簸箩里,只拿剩下一小段芹菜梗去洗。
余锦年看了看脚边簸箩里,已经有许多死不瞑目的菜了,譬如扒得只剩下一丢丢黄嫩菜心的大白菜,揉搓得花头都掉了的椰菜花,坑坑洼洼的萝卜头……
他仿佛听到了蔬菜们的哀嚎:杀父之仇莫过于此了!
季鸿正在认真地“洗”芹菜,忽然感觉身边阴影一重,少年拢起衣摆蹲下来,眉头紧锁着伸手拨了拨木盆里的菜,他不由停下了手里的动作,低道:“抱歉,我……”
从男人看似平静的话音里,余锦年竟听出了几分失落,他抬头看了看季鸿,忽然想到了自己第一次下厨的场景,不禁笑起来。
季鸿一脸茫然地看着他。
余锦年一边把簸箩里的菜挑出来重新摘,一边笑说:“我第一次做菜的时候,是想给我父亲一个惊喜。洗土豆的时候,因为觉得外面很脏,就直接拿刀切掉了一层,最后切得像个桃核,圆葱还一片一片地掰下来洗,被辣哭了眼睛。父亲回来的时候见我在哭,还以为我在外面被人欺负了,气势汹汹的说要去找人家算账。”
虽然上一世的结局令人痛苦,但余锦年这会儿想起来的却都是些令人怀念的事情,且因为自己心态有了些许的变化,没有生病时那么钻牛角尖了,便愈加觉得那些平淡的生活是如此幸福,就连养父声色俱厉地勒令他背书的回忆都带上了一层温馨的颜色。
季鸿见少年洗菜的动作慢了下来,视线从少年的双手看到少年的脸庞,发现那双清澈好看的眼睛当中,竟有些失神无色。
他听二娘说过,少年来到面馆的那天浑身是伤,虚弱得快要死去了,人在床上躺了三天才彻底醒透,又躺了两天才恢复元气下床活动,说那几天的少年还没有现在这样爱笑,总是叫不应,皱着眉头仿佛在思考什么。
季鸿脑海中便浮现出了那样的情景,余锦年伤痕累累和失魂落魄的模样,竟觉得心里莫名紧了一下,也不知道为什么,面前这个少年就像温和的日光一般,在他身边的时候,总让人感到非常舒服,因此他不想看到余锦年露出这样的表情,就好像原本璀璨的星宫忽地黯淡了。
此刻,季鸿特别想摸一摸少年的头,就像少年经常哄穗穗的那样。
余锦年从回忆中恍惚反应过来,似掩饰自己的失态般,此地无银三百两地笑道:“你看我现在,是不是特别厉害?”
突然一阵风刮过,季鸿微微眯起了眼睛,他伸出手去,在余锦年头上虚虚撩过一把,又看了少年片刻,直到风止,才应道:“嗯。”
男人的声音在风的喧嚣余音里显得格外干净清朗,也许是在那一瞬间,乍起的风也带走了那拒人千里的冷意,只留下了无边无际的深沉温柔。
余锦年被风吹得一闭眼,并没有看到季鸿半掩之下的眼神,只觉得头上轻轻被人摸了一下,再睁开,只看到男人手指间捏着的一片枯叶。
大概是从我头上摘下来的,余锦年心道。
“你教我。”季鸿漫不经心地扔了枯叶,指了指盆中剩下的菜。
余锦年忙点点头,干起正事:“这些菜只需要把里面枯黄的、蔫了的叶子摘掉就好,而且把它们在水里泡一会儿,上头的泥土就会松散开来,再洗就容易多了……”
季鸿听得很认真,余锦年很满意,只是不知道为什么,男人视线总往自己头上瞟,难不成自己头上还挂了什么东西?伸手摸了摸,没有啊。
重新洗完了菜,余锦年把菜捧进厨房,也不敢再给季鸿安排什么有技术含量的活儿了。因为瞧见季鸿洗个菜,把鞋都洗湿了,于是叫他坐在灶边一边烤火,一边挑豆子。
余锦年则去找阴阳师父借纸笔。
这里人总有千奇百怪的规矩,这样做席面之前,一般是需要由掌厨师傅列一张菜品清单,先与主人家过目,以防菜色中有什么主家忌讳的东西,有许多农户家其实是不识字的,则由掌厨口头传达,但清单还是要有一个的,为走个过场而已。
新宅尚未建成,想来吴婶娘也没有纸笔,余锦年便径直去寻这些人当中最有“文化”的阴阳师父去。
问了人,都说这位道长是有真本事的,画符祛邪、捉鬼定宅、开场做醮,样样精通,且云游四方归期不定,这日吴婶娘家的能将他请来,是沾了大福缘的机遇。
余锦年“虔诚”地跟人一起崇拜了两句,便直奔道长所在的东屋而去。
此时,这位道长正在东屋正坐上悠闲地品茶,怀里斜揽着一柄刻着阴阳太极图的拂尘,而他面前恭恭敬敬地站着一个四十有余的男人,护着用细麻布包扎着的左手,不停地朝道长敬拜,嘴里念念有词。
他才念罢,道长举起拂尘于半空中一撩,也念道:“驱邪缚魅,保命护身。智慧明净,心神安宁。三魂永久,魄无丧倾……急急如律令!”
道长身形随之一定,之后才慢慢收回拂尘,阖目摆手,缓缓说道:“好了,此符你拿回去,烧融于水后每日分三次与你儿服下,即可除污去秽,保你儿康健。”
男人连连拜谢,又将一锭不小的银子供到桌上:“多谢道长,多谢道长!”
余锦年走进去,闻到男人身上的油烟味,再看他受伤了的手,便猜想他就是那个坏了风水的前掌厨师傅。
道长送走了男人,才端起茶盏,就看见一名少年走了进来,他刚要斥责对方不懂规矩,眼神在来人身上一扫,忽地睁大眼睛惊奇道:“竟有此种气运!勿动,且让本道细细看来!”
吓得余锦年忙站住了脚,任那道长将自己绕了左三圈右三圈。
道长:“稀奇,稀奇!”
余锦年纳闷:“敢问道长,何处稀奇?”
“不可说,不可说。”道长摇摇头,指了指天:“天机不可泄露!”
余锦年也说:“既然不可泄露,那就不问了吧。请问道长,能否借我一笔一纸,好与主人家列张席面单子?”
那道长诧异:“你竟是个厨子?可惜,可惜了。”
余锦年失笑:“那依道长看,我该是个什么?”
两人交谈甚欢,却无人注意到门外又来了一人。
道长皱着眉头,一扫拂尘,深沉低语:“阁下根骨非凡,气运非常,三魂七魄似与凡人不同……”他突然张口大惊,猛退一步,“胎光之主竟已离魂变化!”
余锦年看他手舞足蹈了一阵,又忽地靠近过来,瞪着极大的眼睛问道:“小兄弟,你可愿意入我师门,去往灵山宝峰,学习无上道法,脱离这肉体凡胎?”
“……”余锦年无语了片刻,刚想开口。
“锦年!”
余锦年闻声回头,见是季鸿,正蹙着眉伫立在门旁。
“你怎么来了,我正向道长借——”
“我们回去罢。”季鸿快步走进来,没等余锦年说完,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把他往外面带,“灶上的水沸了,我不会。”
余锦年皱着眉看她。
穗穗才小声哭道:“我梦见一个好可怕的鬼差,它拿着很长很长的链子,它说时辰到了,要来钩我娘的魂……呜……小年哥,我娘她会好起来的是不是?她不会被鬼差勾走的,是不是……”
听到并非是二娘病情发作,余锦年才放心下来,伸手摸了摸小丫头的脑袋,又拽了袖子轻轻擦去她脸上的泪印,安哄道:“有小年哥在呢,穗穗不怕,二娘一定会好起来的。”
梦笔阁免费小说阅读_www.mengbig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