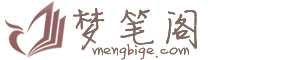正文 第56章 千言万语
作品:《斟万象》 沈攸白昏睡了半日,终于睁开了朦胧的睡眼,花笺察觉到她醒了,拉着她的衣角,小声道:“你昨天出去一整夜,今天又忙着赶路,应该多休息才行。”
沈攸白轻轻摇了摇头,花笺无奈地叹了一口气,放开了手。
马车离了扬州,洪鱼蕉坐在车夫的位置上,一边饮酒一边吹风,好不惬意。
花笺给小书童扯了扯身上的披风,小书童刚睁了睁眼,又朦胧睡过去。书生还是端坐着,闭着眼,像是一截枯木。
沈攸白的精神比那日看起来明显好了很多,花笺把水囊里的水倒在手绢上,让她擦了擦脸,沈攸白擦过脸后钻出了马车,坐在洪鱼蕉身边,却又懒散地闭上眼睛,仿佛不愿从梦里醒来。
洪鱼蕉见她脸色还是苍白,笑道:“我费了老大的劲给你做了胭脂,都没见你用过,你这丫头,真是辜负我洪某人一片好心。”
沈攸白抬了抬眼皮,摸到了胭脂,打开了精巧的盒子,随手点了一些,轻轻在脸上点了点,磨匀了,洪鱼蕉一乐,猛点着头,连续说了三个“好看”。
沈攸白再怎么狠厉,终究是个女子,听到洪鱼蕉这么自己,心情好了些,拿起放在一旁的马鞭,在手里轻轻弯折折,盯着远处发呆。
洪鱼蕉道:“夏恒川那个弟弟是不是欺负你了?输了没事,以后见了他,我帮你找回场面。”
沈攸白咬了咬唇,轻声说道:“那可是公子的弟弟。”
洪鱼蕉嗤笑了一声:“你们这些女人啊,都是口是心非的行家,你这丫头,说不定早在心里把那夏屿青千刀万剐了。”
沈攸白勾起嘴角,露出一个灿烂的笑来,马车擦过垂柳,绿柳拂面如微风,她顺手从旁边的柳树上折下几根柳枝编起来戴在了头上:“心里想的跟实际上做的可不一样,要是人人敢想就敢做,岂不是要天下大乱了?”
沈攸白说完这句,又小声抱怨道:“我倒是想去京城把皇帝拉下来呢。”
洪鱼蕉“啧啧”两声,拨弄着腰上林途寒刻的那个六艺挂坠:“天下人如果都心想事成,果真是要天下大乱的。”
他们这一辆马车路上经过了些城池,始终过城不入,只在村镇当中住宿,必要时才会去城内补充点水粮。原本小书童陶亮最是信息,远远看到城池还神采奕奕,被告知马车不入城之后,虽然觉得遗憾,但还是懂事地点头,每次路过大城时,都趴在车窗上遥遥看着,到底还是孩子心性。
花笺笑吟吟地看着书童,拿起一本书来,摊在膝头,轻声唤他:“读书了,这书中可是有千百座城呢。”
小书童恋恋不舍地收回目光,叹气一声:“曾经听说过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哪来的千百座城?”
花笺道:“以往有个志怪小说,叫《梦梁》的,说是有个读书人,读到了疯魔的境界上,有一天,有两名执笏的礼管从书中飘摇落下,带他走进书里,当场皇帝老儿赐下圣旨,封他为一县县令,这位大人呢?又是个纸上谈兵的空架子,除了读书什么都不会,做县令的时候,说起头一名的功绩,应是在任上读了百千本的书,一县之地内却民不聊生,后来又一道圣旨来了,说他是大材小用,让他去做一州的州牧。这位州牧又是如饥似渴地读书,有一回发了大水,整个州都淹了,饥民把这个读书人围起来,打得他头破血流,他却对这洪水束手无策,等这件事过去,这个读书人请罪辞去了州牧的职位,再也不敢去领官职,干脆在任上就逃开了,一城复一城独自走下去,始终背着自己一箱子比命还宝贵的书。再然后,又有人来捉拿他回去,硬是把他按在一个富庶之地做官”
陶亮嘀咕道:“世上哪会有这么好的事情。”
花笺伸出手,轻轻拧了他的耳朵一下:“还没完呢。这书生后来在一富庶地方上,终于开了窍,皇帝老儿再一道圣旨,把他召为驸马,读书人诚惶诚恐地接旨,嘴上说着不敢,实际上内心里欢喜得厉害。公主嫁过来的时候,城中灯火亮了一夜,道路两旁的树都给火烤焦了。两人一直相敬如宾,有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就在读书人觉得此生圆满的时候,敌国来犯,读书人被派往边境去,他不懂带兵打仗,只是一败再败,亡了国。妻子带着儿女上了吊,读书人最后光着脚走在街头,被百姓痛打了一顿,满头大汗地从梦里醒了。”
小书童陶亮挠了挠头:“我可没听出跟千座城有什么关系,姐姐你是不是唬我的?”
花笺温柔笑道:“这个读书人醒了之后啊,就没有那么爱书了,他开始走出自己的一间书屋,先是负笈游学,后来又前往边境,亲历了战争,才真正懂了民生的艰苦,不是史书当中简简单单写的‘流血漂橹’之类的字,也不是那些个帝王将相的成名史,不是他们如何三千打一万,洋洋得意自己还剩了多少兵马。”
花笺温声款款,小书童却逐渐听得脸色发白,背后全是冷汗,花笺依然微笑,于书生眼神含着赞赏看向花笺。
花笺又说道:“你还小,不要总是读这些王道霸道的圣人之语,你得去看看,每一个小人物,也曾经都是活过的,那一个个在史书当中一笔带过的,甚至是从来没有提到过的人,也曾经是意气风发地活着。”
小书童捧着手里的书,手足无措。沈攸白掀起车帘,投过一个冰冷的目光,也扔下一句冰冷的话:“妇人之仁,成不了大事。”
帘子落下的时候,书童茫茫然看着于书生,不知该如何是好。任何一项政令的推行c任何一场战争c任何一件小事,都可能会涉及到人命,如何让这些人不死如白纸?但如果只念着这些人心中的苦,也是注定成不了大事,除了天上神佛,谁能全这世间所有人的心愿?
花笺见书童如此神情,微微叹了口气,道:“说的太多,偏了正题,书还是要读的。”
于书生拉过陶亮的掌心,花笺也凑过来要看于书生要在他的手中写什么字。
书生写道:“死得其所。”
小书童一皱眉头,什么死不死的,他可不想死。
随即他心有所感,听到了书生的话,心中一亮,如点一盏明灯,瞬时变得清明起来。
加入让天下人都能够死得其所,该是如何一幅图景?
洪鱼蕉原本听花笺一席话,感慨这女人也不简单,又是家国又是讲故事,后来又闻帘子当中静下来,还以为这三人都被沈攸白的“妇人之仁”给镇住了,只不过很快又听到了花笺的声音:“花笺受教了。”
洪鱼蕉问身边沈攸白:“他们说了些啥,花笺就受教了?”
沈攸白摇头:“不知道,我只负责冲锋陷阵,治国是那些文人的事情,但要是治不好,我一样会砍了他们。”
花笺在帘子里缩了缩脖子,对着名义上是主仆,实际上更像是父子的两人吐了吐舌头,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小书童捂着嘴偷笑起来。
洪鱼蕉明知她不会听,还是忍不住教训道:“冲锋陷阵那是男人的事,你就躲在后面好好地给夏恒川缝御寒的袍子就够了。”
沈攸白瞥了洪鱼蕉一眼。
洪鱼蕉唉声叹气道:“也行吧,到时候你负责吸引对面那些个将士的目光,丫头,你要是站在阵前,我保证对面三万个人里头有两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都掉了魂,除非是瞎子,要么就是跟我一样惧内,我们就趁着他们眼珠子都不肯转的时候去,一刀过去砍下他们的脖子。”
洪鱼蕉一拍大腿:“不就赢了?”
沈攸白明明眼带笑意,却龇牙咧嘴,伸手要打,洪鱼蕉理都不理,老神在在地靠在车厢上:“闺女,看着路点,我先睡会。”
夏恒川趴在夏岭的背上,他很想从昏睡当中醒来,明明意识已经醒了,却一直睁不开眼睛,他的眼皮滚烫,背后更有一团火在燃烧,随时像是要炸开,夏恒川努力挪动了一下手指
夏岭察觉到背后夏恒川的异动,轻轻压下了他浑浑噩噩想要抬起来的那只右手,夏屿青视如不见,林途寒见了这一幕,笑容玩味。
夏岭叫夏屿青道:“屿青,给他喂一口水。”
夏屿青身前牵马的小蕊闻言摘下水囊走到夏恒川身边,她长了一张很讨喜的娃娃脸,笑起来的时候活泼可爱,这下正笑着给夏恒川喂水,仿佛夏恒川打成这样的并不是她。
小蕊踮起脚来给夏岭喂完了水,又回去牵马。
夏屿青转身道:“爹,把他放到马上吧。”
夏岭摇头:“马上太颠簸了。”
前面小蕊在地上摘了一朵花插在鬓角,没心没肺地哼着歌走在前面。
林途寒抱着臂,看着那个女孩,轻道了一声:“夏家人才辈出。”
夏岭道:“拙荆留下的一个身世可怜的孩子罢了。”
夏屿青听到这句话,回头看了一眼林途寒,却瞥到了跟自己背道而驰的扬州城,书里看来的,毕竟不是眼前的东西,他有些许遗憾:“都已经走到门前了,却还没来得及走进扬州城中去看看。”
夏岭道:“以后有的是机会。”
他又说道:“现在的扬州,算不上是什么值得看的地方,二十年前真倾国,如今无梦可还家。”
夏屿青脸上出现一丝动容,他笑道:“朝中呆久了,酸腐气很重。”
夏岭说道:“我在朝中才是长了见识,暗中的刀剑,比明处的刀剑更加伤人,都说那些佣兵的武人乱国,实则读书人能治国,读书人也能误国,只不过一张嘴一支笔在他们那放着,由着他们说和写而已。”
小蕊摘了一阵花,等几人走过了自己的身边,跟在夏屿青身后蹦蹦跳跳地走,天真问道:“少爷,要不然我再出一次手?”
夏屿青继续向前走着,没有答应,也没有不答应。
夏岭却如没听到这句话,没有任何反应。
小蕊的脚步顿了顿,落后了几步,又再次跑着跟在夏屿青身后:“以前大少爷买蘇柳那家铺子里的糕点,也会分我几块,现在我还想再吃一次。”
夏屿青轻轻勾了勾嘴角,从马上挂着的袋子中摸出一个油纸包。
小蕊托在手中,天真地笑道:“我就知道少爷不会忘了这件事的。”
她撕开油纸包,毫无吃相地往嘴里塞了几块已经被压坏了的糕点,吃得满嘴油腻,一路飘香。小蕊吃了一小段路,最后还剩下几块实在吃不下了,抬头鼓着腮帮子看着夏屿青。
夏屿青随手接过来,下解决了剩下的两块。小蕊俏皮地打了一个饱嗝,把马缰递给了夏屿青。
夏恒川上了马,纵马向前跑去,只跑了小两步,又折回来,下了马对小蕊轻轻点了点头。
走在最前面的夏屿青,也已经能隐隐有所察觉前面那人的气息,如黑云压城,蓄势待发。林途寒收敛了一路以来的轻松神色,夏岭把夏恒川往上颠了颠。
林途寒轻声道:“来头不小。”
小蕊摘下鬓角那朵行路途中已经快枯萎的花,笑道:“少爷我去了。”
夏屿青一言未发,小蕊却笑着说道:“少爷以后自己要好好的,在府里,以后除了老爷,就得听您的了。”
小蕊转身面对夏岭林途寒两个人,跪在地上,磕了一个头。她站起来之后,身上气势猛然一凛,裹挟着一股巨大的气劲,如一道冬风劲扫春日。
小蕊随手拔出一棵细细的小杨树在手里作剑,直直向着夏岭背后的夏恒川刺去,不顾林途寒已抽长恨,也不顾夏岭出蛰冬一剑,以鱼死网破的架势去跟两人拼命。
林途寒的长恨去挡小蕊的“剑”尖,夏岭一扭身,让身后的夏恒川避开,手中的蛰冬已穿透她的肚子。
夏岭脚下一片草由内向外倒伏,夏恒川仰面躺在地上,夏岭被小蕊手中树崩断时的气劲冲及心脉,顾不上自己,赶紧回头去看夏恒川。
林途寒拄着刀看着前方,静等一个人出现。
大路上,走过来一个双手揣袖的人,那人脸上满是喜色,看到这一行人,加快了脚步,他走到夏岭身边,神色谄媚,面白无须的脸像是剥了皮的老鼠。
他声音尖利地喊道:“大人哪,圣上知道大人家里出了变故,让我出来帮忙,没想到没赶上。”
说着,他伸手叹了叹夏恒川的气息,笑得喜不自胜:“夏大人放心,还能活。更何况这一门二俊彦,前面那个,比这个还好。”
夏岭听着他这句话,也没说什么。
钱宜伸出脚踢了踢腹中流血的的小蕊:“可惜了这个一个可人儿,大人还是赶紧回去清查府上,看还有没有窝藏祸心的家仆,这些人啊,就不能对他们太好,好过了头,就反倒骑到咱们头上来了,是不是?”
夏屿青牵着马反身回来,把小蕊放在马上,对这年轻宦官钱宜说道:“让大人见笑了,她就是见我被夏恒川欺负,觉得咽不下这口气,这次才出了一记谁都想不到的后手。”
钱宜面皮惨白,阴柔柔笑道:“你也是,让你爹这么不放心。”
夏屿青一揖道:“屿青正是因为大哥总让爹担忧,这才跑出来找他,跟他说定了,我赢了他就要回家不再游历江湖,没想到竟然出了这等事,让大人见笑了。”
钱宜又细声细气笑道:“行了,都快些回家吧,这世道,还是家里好,走在外面,谁知道哪天就被人给砍了脑袋。”
钱宜刚要转身,就见夏岭一剑刺在小蕊的心口,夏屿青骇然一动,双手紧紧在袖子下握成了拳头,这宦官故作惊讶道:“夏大人这是干什么?”
“不听话的奴婢,也没必要留着。”
钱宜叹气摇头,揣着手又走远,走了几步又退回来,朝向林途寒,问道:“这位是?”
“犬子的师父,魏舒泰在外被人伏杀,这不又给恒川请了一个师父,教他一些武艺,强身健体,以后主持夏家,在铃吾没有一点武功可实在站不住脚。”
钱宜眯着眼打量林途寒,林途寒脸上刀疤一皱,笑说道:“在下从北边饮马关来,在那边能查到户籍,大人如果不放心,尽可以去查。”
“咱家只是想起夏家大公子不喜练武的传闻。”
这名宦官说完这句话,眨眼之间已经是十丈之外,几人目中再无踪迹。
夏屿青牵着马,马背上的小蕊已经死透了,身体发凉,双眼紧紧闭着,睫毛上沾着一些泪水。
夏屿青面无悲痛,亦无不忍,隐忍到了一种极为可怖的境地:“爹,我去埋了。”
林途寒伸出手一拦:“还有的救。”
林途寒想知道,夏屿青这个人究竟还有什么真正放在心上的东西,一旦心中有了牵挂,就有了弱点,夏恒川弱点太过明显,多情又念情,夏屿青则冰冷不近人情,似乎总是在刻意拉开跟其他人之间的距离。那年在铃吾,先见到了夏恒川,又见到了夏屿青,夏恒川优哉游哉度日,夏屿青日日不曾懈怠,夏屿青,究竟是个什么人?
夏屿青冷冰冰的脸上没有任何情绪起伏,牵马走到林途寒身边:“那就麻烦先生帮忙救救,她要是还能活下来,就让她别再回来了,活不下来了也就算了。”
夏屿青说道:“作为回报,我保证夏恒川不死。”
林途寒道:“亏本生意。”
夏屿青把马缰递过去,再没有说话,林途寒从他手中接过马缰,带着小蕊走了另外一条路。
夏屿青蹲下身来,夏岭把夏恒川放在他的背上,叹了口气。
夏岭与夏屿青并肩而行,夏屿青比夏恒川要矮一些也瘦小一些,夏岭看他背着夏恒川,仿佛被一座山压了头,心中未免凄恻。
夏岭挽了挽袖子,说道:“屿青,还是我来吧。”
夏屿青低头走路,他在爬上一个缓坡之后用力呼出一口气,语气平静地说道:“现在,我什么都没了。”
夏岭跟他并肩站在缓坡上,说道:“以后都还会有的。”
夏屿青简单“嗯”了一声,继续低头向前走去,仿佛把头埋进了地上。
这一路走来,夏岭发现自己越发看不清夏屿青,以往他觉得夏恒川夏屿青两人,一个是外热内冷,一个是外冷内热,如今看来,或许是自己错了。
夏岭在夏屿青手背上轻轻一拍,夏屿青微微弯起嘴角,单薄地笑了笑,夏岭又道:“以后都会有的。”
夏岭说完这句话,在嘴角再叁回味,越发觉得这话意味的淡薄,它也仅仅只是一句话而已,甚至连句承诺都算不上,再说屿青,大概也不会信吧。
夏岭在临近的镇子上买了一辆马车,让两个儿子在车厢里,夏岭亲自做马夫载着他们回铃吾去。
夏屿青歪在车厢里看着仿佛睡着了的夏恒川,不再掩饰自己脸上的疲惫,窗外天上,黑云浓重,滚滚有雷声仿佛自千里之外的平地上生出,已是山雨欲来的趋势。
夏屿青背后一双苍白透明的手伸出,弹出两滴甘露落在夏恒川嘴中。夏恒川胸口一团紫雾蒸腾,久久不散。
林途寒握着马缰,走在这细雨当中,见自己手心有血低落,他松了松手,马缰滴血如泣。
夏屿青展开手心,手心一道伤口深可见骨。
心头千言万语,头顶不过一场春雨,一场春雨而已。
(本章完)
梦笔阁免费小说阅读_www.mengbige.com